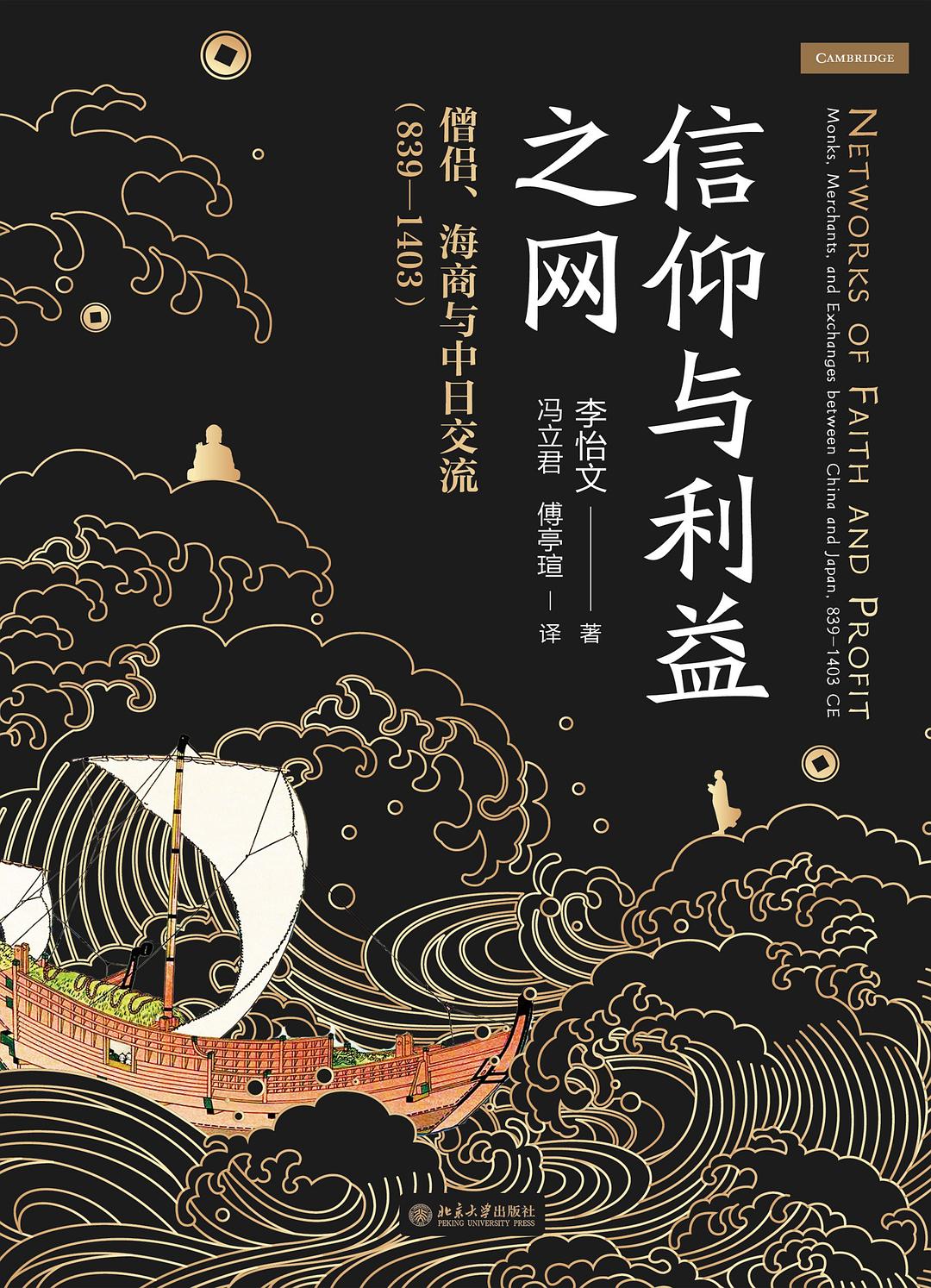
《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李怡文著,冯立君、傅亭瑄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240页,80.00元
香港城市大学李怡文副教授的新作《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近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冯立君教授翻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一名以日本中世政教关系史和九至十五世纪东亚海域史为研究兴趣的后辈,笔者去年就注意到了李怡文教授大作的出版信息。无论是839-1403年这个时间段,还是入宋僧、博多纲首、寺社造营料唐船这些关键词,都让笔者倍感熟悉。新书到手后,便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李怡文教授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京都大学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地访学。这部著作是李教授在美国撰写的博士论文,题为“信仰与利益之间”,将僧侣与海商,或者宗教与商业作为全书的关键词。宗教与商业网络的关系,很早地就在中日关系史和东亚海域史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比如本书引用过的国际日本文化中心榎本渉教授的《僧侶と海商たちの東シナ海(僧侣与海商的东中国海)》(讲谈社,2010,2020年以文库本的形式再版),就直接将“海商”和“僧侣”放入了书名。许多研究中世佛教史的日本学者,如原田正俊、横内裕人、上川通夫等,也乐于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讨僧侣与海商活动的关系。谈论中国与日本列岛的联系离不开僧侣与海商这两个关键词,甚至可以说,前近代中国与日本各种形式的交往,绝大多数均以海商和僧侣为媒介,与宗教信仰的传播和商业网络的扩散密不可分。
学术界对于海商与僧侣关系的强调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史料的限制,由于九至十四世纪海商活动本身缺乏一手史料,贸易史学者经常需要依赖搭乘商船渡海的僧侣留下的记录,来复原海商活动的点滴(参考榎本渉编《南宋·元代日中渡航僧伝記集成[南宋·元代中日渡航僧传记集成]》,勉诚出版,2013)。
东亚海域贸易史现在已经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学术影响力的国际性学科。在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九州福冈市的博多遗址群考古的进展和韩国新安沉船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对宋日、元日贸易的研究。特别是在“宁波项目”(全名:“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2005-2009)以后,关于前近代中日贸易的形态、规模、商品、参与人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李怡文教授对东亚海域贸易研究的开始,想必也受到了“宁波项目”的间接影响。特别是迄今为止,在关于“博多纲首贸易”的研究中,唐房的形态,宋商在博多当地与显密寺社网络的密切结合,“博多纲首贸易”向“寺社造营料唐船贸易”过渡的原因与过程,及其与禅律留学僧的关系,乃至民间信仰通过宋商活动的传播等,均已得到了比较多的讨论。代表的研究者在日本有村井章介、川添昭二、渡边诚、榎本渉、山内晋次、田中史生、关周一、伊藤幸司、大塚纪弘、西谷功、中村翼等,国内则有王勇、江静、陈小法、赵莹波、郝祥满等。本书所涉及、讨论的是一个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都十分热门的话题。并且,相较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李怡文教授的欧美学术背景使得本书具有了更多的理论性和比较研究的色彩。
本书提出了“宗教-商业网络”这一重要概念。作者将其定义为被信仰鼓舞的僧侣与由利益驱使的商人一同建立的非官方贸易网络,持续时间是九世纪至1403年。并且,本书还将其视为朝贡关系的替代物。本书批判了仅以朝贡体系的观点来观察东亚世界的思考方式,指出随着九世纪以后中日朝贡关系的衰退和海商贸易的发展,“宗教-商业网络”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最终取代朝贡关系,成为中日间最主要的交流渠道。本书更进一步讨论了“宗教-商业网络”对朝贡关系的替代的各个历史阶段。比如,在北宋初期还能看到朝贡时期的残余(奝然的例子),但非官方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开始愈发重要。随后,大量中国海商在日本扎根,僧侣与海商的合作发展出更为复杂和深入的联系。
本书所强调的“宗教-商业网络”是一种因僧侣和海商渡海活动的推动而扩散的跨境人际网络。但其产生,一开始源自中日两国内部佛教寺院与商人、当权者的互动。作者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日僧圆珍和海商李延孝、唐僧义空与徐公祐、东福寺圆尔和“博多纲首”谢国明的合作,以及宋代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板渡”一事中径山寺僧人德敷的活动,作者把他还原到了江南禅林、地方士绅、官府与海商的互动之中,十分有趣。作者还多次利用中国史料,使用宋代对外贸易的一些其他事例做了对比。
通过这些事例的分析,本书还原了“宗教-商业网络”发挥效用的背后原理和机制。首先,政府对对外贸易有严格的控制(中国有市舶司贸易,日本有大宰府管理体制),但借助与当权者的密切联系和所拥有的宗教资源,佛教寺院可以找到规避限制的方法;当商人遇到麻烦时,也可以通过佛教徒寻求帮助,与当局交涉。并且,在中国和日本,世俗当权者和有权势的寺院都有合作关系。因此,商人、世俗当权者、寺院由此联系起来,并通过跨境僧侣和海商的活动形成跨越东亚海域的庞大“宗教-商业网络”。中国的海商利用这一网络建立寺院,日本的当权者也利用这一网络向僧侣提供赞助。进而,中国和日本的朝廷都充分意识到了佛教僧侣和海商之间的合作关系,认识到这一关系网的价值,把这个宗教-商业网络当作沟通的非正式渠道。这一发达的网络最终为十五世纪的朝贡贸易奠定了基础。1403年以后,僧侣继续往来于中日之间,传递信息,起草外交文书,成为朝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
本书所提出的“宗教-商业网络”,敏锐地捕捉到了九至十四世纪中日关系的关键要素,准确阐释了维系东亚海域交流的核心机制,有力地回答了中日关系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遣唐使的时代结束以后,为何看上去封闭、孤立的日本列岛仍然没有和东亚世界彻底隔绝?明朝拉启海禁的大幕以后,日本为何又能迅速转向朝贡贸易,并建立独具特色的“五山外交”?通过史料的梳理、史实的还原,本书将“宗教-商业网络”这一替代朝贡关系的非正式渠道的发展脉络一步步呈现出来。笔者曾在《中世の禅宗と日元交流(中世的禅宗与日元交流)》(吉川弘文馆,2021)的末尾部分也试图讨论了东亚海域交流中的跨境人际网络。笔者所关注的时间段主要是南宋至元代,认为中日两国当权者能够将这一人际网络用作获取和传递信息,乃至开展外交活动的渠道。出于强调禅僧在人际网络中的核心纽带作用的目的,将这种非正式渠道称作“江南禅宗文化圈”的跨境人际网络。笔者与本书一样,都强调世俗当权者对这种跨境人际网络多方面的利用。虽然元代中日贸易极少有海商的名字见诸史料,日本的公武当权者在贸易中的重要性超过了海商,但仍无法忽略海商的活动。
另外,本书还强调了“宗教-商业网络”的物质性。特别是在东亚海域贸易史讨论较多的硫磺、铜钱、瓷器等商品之外,作者指出了佛教物品在其中的重要性。比如佛教的法器、佛像、藏经乃至寺院的匾额、书法作品。这也正好是笔者近期比较关注的地方。窃以为,本书是中文学术界出版的一部十分精彩的前近代中日关系长时段研究著作,能够给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带来很多的启发。借此机会也对本书译者冯立君教授、傅亭瑄同学表示感谢。
但是,或许是受限于篇幅、题材等方面的限制,本书仍然还留有一些缺憾,让人读起来有些意犹未尽。以下,笔者也想就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疑问和困惑,在此与作者讨论。
首先是本书所引的史料。本书的主要史料是僧侣的旅行记(但这个时代存留的旅行记很少,篇幅较长的仅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参天台五台山记》)、信件、传记及寺史。但是,通读下来,本书的史料引用仍少于同问题框架下一般的研究著作。在史料的选择方面,中国史料比较多,日本史料相对较少。特别是日本史学界重视的“一次史料”(即初级文献、首次文献或一手文献,指还未被资料创造者以外的人改写或诠释过的史料)中利用最为广泛的古记录、古文书史料的引用频率比较少。引用的日本史料,以五山僧的传记和《元亨释书》《扶桑略记》等史籍为主,《镰仓遗文》的引用仅有三次。古记录方面《御堂关白记》有三次引用,却没有《小右记》,也没有镰仓时代的公家日记。但海商和渡海僧侣在古记录、古文书史料中出场频率并不低。本书中提到的多位海商,多次贸易活动,实际上就有古记录史料的记载。
其次,关于海商与僧侣的合作关系方面,本书的叙述缺失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本书认为世俗当权者和有权势的寺院都有合作关系,僧侣和当权者的关系也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但是,这需要更为详细的探讨:为什么僧侣可以与当权者建立联系?这不仅仅是因为僧侣所在的寺院与当权者之间的联系,也不仅仅是因为当权者信仰佛教。既然是探讨人际网络,不能只讨论网络如何发挥作用,还需要搞清楚人际关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比如入宋僧寂照,原本就是朝廷中的文章博士,俗名大江定基,贵族社会的一员;入宋僧庆政,可能是摄关家出身;镰仓时代很多入宋、入元留学的僧侣,其俗家出身是幕府御家人。本书对具体的海商和僧侣的出身背景缺乏介绍,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三,关于“宗教-商业网络”在十四世纪的变化的问题。十四世纪是中日贸易、中日交往的又一个分水岭。大规模跨境留学、巡礼的热潮消退,本书认为,倾向于禅密兼修的梦窗疏石及其法脉的崛起,标志着中日之间密切的宗教交流已经开始减弱,日本僧侣不再有到大陆学习的强烈渴望。但事实上,梦窗疏石并非对中国“兴趣不大”,其门人中有多位入元、入明者,即便这些禅僧回国后大多嗣法梦窗,但嗣法更多反映的是禅僧政治性、宗派性的考量,若从参学、交友的角度来看的话,梦窗门流对渡海参学并不排斥,而梦窗本人对迎请中国禅僧到天龙寺也十分欢迎。当1374年日本禅僧再度获得机会前往中国时,他们的热情并不亚于元代。但因为明代对外政策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留学僧的热潮终于停止。因此,“宗教-商业网络”在十四世纪的变化与其从禅宗内部寻找原因,倒不如应该讨论该时期东亚海域秩序变动的外部因素。
第四是一些细节的史实问题,主要是关于日本史的一些史实,大概是作者稍微有些疏漏的地方:
一、第59页谈及寂照时,作者称“从到达中国开始(1005),寂照就利用非官方的网络与日本高层当权者保持联络,特别是藤原道长——当时日本的太政大臣和实际权力的拥有者”。但实际上,藤原道长担任太政大臣是1017年(次年辞任),在1005年时,道长的官职是左大臣。由于太政大臣在名义上是日本朝廷的最高官职,所以容易让人产生其是权臣所应担任的官位的误解。第61页亦然,里面说“太政大臣藤原道长赐予曾令文登陆的特别许可”。但这时的藤原道长仍然不是太政大臣。藤原道长甚至这时连摄政、关白都没有担任。
二、第123页称“九条道家授予圆尔圣一国师称号”。这大概作者是依据《圣一国师年谱》的记载得出的结论。但《圣一国师年谱》的原文是“(九条道家)亲书圣一和尚四字,以拟唐代宗赐法钦国一之例”,这里的“圣一和尚”并不是“圣一国师”的意思。一方面,纵然权倾朝野,国师号的授予仍不在九条道家职权范围,而是需要天皇的敕旨,或至少有上皇的院宣,通过朝廷的正式手续才能完成。另一方面,圆尔被授予“圣一国师”的称号时间非常明确,是在这条记载之七十年后的1311年,经东福寺申请、镰仓幕府推荐,在东福寺僧藏山顺空、无为昭元、南山士云等的多方奔走之下,才获得了伏见上皇的院宣(国师号宣下)。国师号宣下是东福寺历史上的大事件,能够获得成功,十分不易。再者,《圣一年谱》这段关于九条道家与圆尔对话的记载中,还提及九条道家想要授予圆尔“日本国总讲师”与“僧正位”一事,因与当时日本佛教的制度不符,可信度存疑,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慎之又慎。
三、第133页称“执权代替年幼的幕府将军统治镰仓幕府”。这大概是对执权政治的一个误解。即便在最初的源氏将军(赖家、实朝)时期,执权行使对镰仓幕府的统治权的缘由都不是因为将军年幼。
四、第154页称“后醍醐在足利兄弟夺取权力后,他被流放至吉野山”。但实际上后醍醐并不是被足利(尊氏、直义)兄弟流放的,而是自己跑到了吉野。后醍醐之前曾经被镰仓幕府流放过,但流放地是隐岐岛,不是吉野,也和后来同足利兄弟的对立无关。
五、第158页关于天龙寺落庆供养法会的描述很不准确,实际上延历寺反对的是天龙寺落成法会的规格过高(准御斋会),而不是反对法会本身。且延历寺反对的对象也不是本书所提到的“追悼庆典”,那是同月举行的另一次仪式(后醍醐天皇七回忌),而是天龙寺的落成仪式,两者虽然旨趣相近,且时间就差了两星期,但在当时却是明确区分的不同仪式。另外,本次事件称不上“给足利幕府提供了一个加强控制(延历寺)的契机”(158页),只能说这次事件给幕府“试图加强对延历寺的控制”的努力提供了契机而已。
以上是笔者一些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方,放在整本书简洁明快、流畅清晰的叙述中,几乎微不足道。本书在中文学术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相信今后一定会成为国内研究中日关系史、东亚海域史的必要参考书。“宗教-商业网络”也必将在更多的角度下获得不断的讨论。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